疫情下孩子回不去球场!他们在小区空地、苗圃园踢球,广场舞奶奶让路
疫情来势汹汹,提醒人们谨慎与清洁,也让为“目的”而忙碌的芸芸众生些微停下脚步。疫情缓解,孩子们像鸟儿出笼,就算回不去学校上不了球场,但他们在花园里踢球,在苗圃里奔跑,在广场上与奶奶们交换雀跃的心得。这些就像春天的雨夏天的风,让人在欣欣中,诚实观己,相信生活。
“快来啊!我要当守门员!”
“我们几个一起,你们几个一队!不能带年龄大的孩子。”
周末的下午,望京小区里,十几个孩子在社区的小广场开始分拨踢球。两个电灯杆恰好和花园的围栏构成了球门。
这里就成为了孩子们的足球场。
“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的一样,放学回家,书包扔家里就在胡同里踢球。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”智斌是一名足球培训机构的教练,因为疫情,机构始终没能为对口的学校授课。每天,他都带着儿子在小区花园里这样踢球。看着孩子们享受足球的快乐,他也想到了自己的童年。
设计/王烨
01、小区的空地,成了幽暗焦虑中的一点亮光
张润春是七一小学校队的学生,因为4岁就开始踢球,所以比其他孩子的足球水平更高,也是校队的球星。司职中场的他,曾经一场比赛攻入了对手六七个球。
这天下午,他跟着父亲从海淀到望京的小区来踢球。他也是智斌培训校队的一名学生。别看孩子们只有10岁大,他们也很清楚在过去这几个月发生了什么。
“一开始不能踢球,真的挺伤心的。”润春家住在大院里,有一个小足球场可以踢球。但是因为疫情暂时关闭了,疫情刚刚缓解之后,他就跟小伙伴一起翻过栅栏去踢球。
“能和大家一起踢球的感觉真的很好!”场上活泼,场下的润春说话很是沉稳。
一个胖乎乎的男孩从远处跑过来,手里拎了个袋子。一路喊着:“我要当守门员!”说着从袋子里掏出了一副手套。“这是我自己准备的,因为我平时就喜欢打羽毛球、乒乓球,我觉得我守门应该比踢球更好。”
男孩儿的奶奶刚刚买完菜从这里经过:“一会儿给你炖红烧肉啊!踢完记得早点儿回来。”老人说完,拖着买菜车就离开了。
原本小区里这片空场是给老人跳广场舞的,疫情缓解之后,几个孩子开始在这里踢球,老人们就自觉让出了这块地。现在,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每天下午固定两个小时,这里就是踢球孩子们的乐园。
小区的空场,成为了孩子们的“临时足球场”
嘉泽是智斌的儿子,或许正是继承了父亲的足球基因,嘉泽跟同年龄孩子踢球,技术水平也更胜一筹,一个人盘带可以连过五人。“每天最开心的就是在这里踢球,要是能赶紧踢一场正式比赛就好了。”嘉泽说。
疫情爆发,别说孩子们,就是智斌这样的大人也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困难。机构运营的压力空前,眼看要成行的西班牙足球游学也打了水漂。
大家都处于深深的焦虑中,但小区楼下这片场地突然给了他希望。从起初只有自己儿子一个人,到后来小区里越来越多的孩子被足球吸引。有些孩子之前根本没有踢过球,看着好玩儿就加入进来,智斌有时候也会带着孩子们玩玩,教他们一些简单的动作。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学习班。人多的时候,还必须得轮班才能踢上。
“能够就在家楼下踢球,这画面其实好多年没有看到了。我们小时候不就是这样么?哪儿有什么专业的足球场,就是每天在胡同里跟小伙伴踢球。疫情虽然对大家的生活都有影响,但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足球最初的本真,其实挺好的。”智斌说。
02、苗圃里拼接出的临时足球场
60多公里外的窦店,刘泽英正带着王昌宇在一片树林里练守门。
刘泽英曾经是70年代北京队的守门员,退役之后一猛子扎进了校园足球的圈子——当然,那个时候还没有校园足球这个概念。多年过去,他带过的张思鹏、侯森都已经成为了职业赛场上的球员,而他从未离开校园足球领域。
王昌宇是刘泽英发掘成守门员的。当时刘看到窦店当地小学足球队踢着玩儿,王昌宇在其中表现出很好的身体协调性,于是他找到孩子家长,建议孩子改练守门员。在他的带领下,王昌宇进步很快,被特招到了清华附小,如今他的能力在北京市内同龄的门将里能排到前三。
疫情袭来,训练中断了。王昌宇的父亲王强在窦店有500亩的苗圃,他跟刘泽英合计着,在家里的苗圃园圈出一方10米*10米禁区大小的地。疫情期间没法买真草坪,王强就网购了几块人工草皮拼接在一起,自己铺上颗粒。没有现成的球门,两个人就用钢管,一段一段焊接在一起,拼成球门,再搭上球网。前后总共只用了三天的时间,就给孩子DIY了一块临时训练场。
苗圃园里自建的足球场
“孩子踢足球,最终要的就是两个‘长’——家长和校长。这两个‘长’不支持,孩子是不可能踢出来的。“刘泽英一边训练,一边跟记者聊着。
球场搭成后,有时候,其他孩子也会跟着刘泽英来这边训练。刘泽英在门前训练孩子,王强就在旁边帮忙递球。场地虽是临时的,但训练一以贯之,风雨无阻。
疫情爆发之前,王昌宇基本每周一到周四都是跟着刘泽英在清华附小训练。学校复课之前,家门口的这块地让他能够保持训练。这里面有着父母的用心良苦,也有着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执着。
王昌宇在进行扑球训练
守门训练在外人看来有些机械,因为快速反应背后是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动作形成的肌肉记忆。但小小年纪的王昌宇可不嫌它枯燥,他说自己以前在学校里踢球就像“起哄”,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应该在哪。按照守门员的方向训练之后,他也发现了自己的价值,练起来劲头十足。
王昌宇的偶像是德国门将诺伊尔,他也特别坚定自己能走上职业球员这条路。虽然老父亲对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笃定,但他还是想尊重孩子的意愿。王强也笑称,这个临时的足球场会一直保留,算是给儿子踢球留下的纪念。
03、孩子们开心就是我们最开心的
5月下旬的一个周五,程璐回到了自己足球俱乐部的办公室。拉开窗帘的一刻,好像是插上了战旗,又要重新战斗了。
原本俱乐部对口海淀区几个足球特长校,也真正培养了一批孩子。原本今年春节一过,就打算带着70多个孩子到西班牙踢球游学。计划已经做了很久,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这次行程也像是一次朝圣。
随着疫情的加重,大年三十那天俱乐部不得不被迫取消了航班。
“后来家长说,好多孩子在家都哭了,而且哭的很伤心。孩子们太想出去跟同龄的人比比,想要看到和世界顶尖足球国家的孩子有什么差距。但是却没去成。”
跟很多培训机构一样,疫情的到来,给整个机构的经营带来了致命的打击。整整四个月,几乎零收入。但让程璐感动的是,机构里没有一个人离开。
他们的教练中有职业运动员出身,也有从校园足球成长起来的受益者。四个月里,大家每周会开例会,想各种办法让孩子能够坚持锻炼。于是,网上打卡成为了他们首选的一种方式。
王桂生是北京最早做基层校园足球工作的老教练,程璐的培训机构里的教练很多都是王桂生的徒弟。原本已经退休的他,因为离不开孩子们,选择在弟子的培训机构和海淀区一些小学继续培训孩子踢球。
最早曾经是体校出身,赶上78年恢复高考他就读了书,82年毕业也没再走专业道路,觉得教教孩子也挺不错。没想到一干就是一辈子。王桂生说,曾经想过换个工作。但是一波孩子走了,又来了一波更好的孩子,总是有那么多优秀的孩子一波波地送到他手边,于是他这辈子也没离开这份工作。
采访那天碰巧遇到王桂生从外面回来,在报箱里取了《足球》报。这报纸他从80年代订阅到现在。他习惯于传统的生活方式,没有像有些老人那样用智能手机浏览新闻。
手拿《足球》报的王教练
在疫情出现之前,他还不会用微信。但培训机构组织孩子微信打卡,督促大家不要荒废居家隔离的时光,王桂生为了孩子们,才开始接受微信这个新事物。
“我们让孩子颠球,孩子们就开始自己比赛,有了这个氛围,就能更好的督促他们提高,特别好。”
微信群里的打卡训练
前音乐人欧秋亭现在成了足球教练。看到他穿着一身运动服,戴着棒球帽,都有点想不起他做音乐的样子了。他说这辈子就会做两件事:踢球和音乐。踢球方面,小时候受过专业训练,跟北京最早的一批职业球员当过队友。后来受家里影响,改去玩音乐,给很多大陆一线歌手写过歌。在音乐圈折腾了很多年,现在却还是选择回到足球圈。
“我喜欢跟孩子在一起的感觉,特别的单纯,没有负担。”欧秋亭说。居家隔离期间,为了更好地督促孩子们训练,欧秋亭没少花心思,踢卷纸打卡,或者设置小奖励,都让孩子们玩得劲头十足。
孩子们的单纯和快乐,也激励和感染着大人们。
我们走访的所有基层教练都说,自己最开心的事情,就是看到孩子们通过足球找到快乐或者实现梦想。成为职业球员,或者依靠足球考学,并不是踢足球的唯一理由,甚至不是最大的理由。
当家长们在纠结踢球和学习孰轻孰重时,我们走访的教练异口同声:我带过的孩子里面,踢球踢得最好的,往往学习也都是最好的——“脑子不好,踢不好球。”
疫情挤压了人们生活空间,却也因此让大家猛然发觉,街头巷尾的孩子们自然而然地踢起球,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,才是快乐的本真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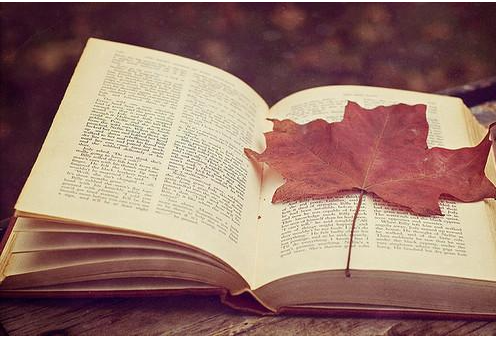



 diyizixunwang.com All Right Reserved.
diyizixunwang.com All Right Reserved.